哲学家擅长说理,他们往往从直觉出发对所谓的深刻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在这样的说理过程中,他们会援引一些例子作为支撑性论据,有时候动物会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之中。但哲学家们并未给动物们发言的权利,它们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人类的偏见或错爱。马吉欧里的《哲学家与动物》一书就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不同的哲学家笔下的动物是如何被用来支持他们的说理活动的。而哲学家们对动物的论断往往反映了他们对某些哲学问题甚至人类自身境况的认识。
谈论一个对象,首先需要对其命名,命名这种行为将对象安放在某种权力秩序的合适位置。人类的语言自然反映出人类所理解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的中心是人类,其他动物、植物、东西依次排列开去。而“动”物一词则表达了人们在这种秩序安排上的游移不定。马吉欧里在本书后记中提到,动物之所以被称为animal,原本就透露了某种迟疑(拉丁文的anima意思就是“生气,生命”):动物就只是会“动”的物?“会动的物”这种表达代表了动物居于人与物之间的地位。而哲学家们对动物的看法也莫衷一是。
首要的问题是,动物是否有心灵(灵魂)?思想史上的许多哲学家都认为,人是有心灵的存在;而动物没有心灵,仅是像机器一样的存在。西塞罗认为,动物只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某些任务而存在:马为了载重,牛是为了在田里劳动,狗则是为了打猎和看家。笛卡尔则进一步直截了当地指出,动物没有心智和语言能力,它们只是机器。
笛卡尔的结论大概来自他对知识起点的探索。他通过普遍怀疑方法排除掉一切可疑的知识,最终仅剩“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即人对“自己在思考”这一点是无法被质疑的。而笛卡尔只是从语言层面“论证”了“我”是有心灵的存在,但却将他人和动物是否有心灵划入了被质疑的范围。也正因此,笛卡尔之后,哲学家们才需要费劲地论证“他人之心”的存在,这在常人眼里不得不说是一桩哲学丑闻。
但也有少数哲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蒙田在动物是否拥有心灵的问题上则更为谦逊;他认为,尽管我们无法与动物交流,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动物没有语言和心智。这种观点更有点庄子“子非鱼”的味道。
我们从《哲学家与动物》大致上能看出,越是古代的哲学家,越是会在人与动物之间划上明晰的界限。但事情在达尔文的演化论出现之后就开始起了变化。动物是否有心灵已经不再是一个直觉、概念层面的“证明”问题;这个问题逐渐被生物学家等领域的实证研究者接手。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许多动物都有十分丰富的交流系统,甚至像黑猩猩、宽吻海豚、亚洲象等一些动物甚至都能认出镜子中的自己,在这些证据面前,哲学家们似乎再难以斩钉截铁地说动物没有心灵了。
多少有些无奈的是,动物们自己并不能申辩它们是否有心灵,这需要哲学家们的“论证”。动物是否有心灵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如何对待它们,当哲学家们认为动物与人之间界限分明的时候,动物的福利问题尚未被提上哲学议程。彼时的动物也仅仅是会移动的“物”,就像古希腊的奴隶也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样。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各种动物种群的延续只能是近现代的事情。
古代人只会通过远近亲疏确定自己对待动物的态度,这一点十分类似于费孝通先生解释的中国古代伦理传统“差序格局”。根据人类学家的记载,这种伦理关系格局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族群中都能找到,它几乎就是人类天然的思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离人比较近的猫、狗等动物自然会受到特别的照顾和对待,甚至人们会将其当作家庭成员,进而享有部分“人权”。
我们现代人比较喜欢谈动物福利、动物权利。但我们要知道,如果权利无法实现那就只能沦为空谈。因此,权利的前提是能够实现它。而权利的实现需要许多外在的条件。人类从提出平等、自由的口号到现在也没能充分实现权利;而动物福利论者则又匆忙地赋予动物以人类平等的权利。事实上,以目前人类的发展状况而言,我们还无法充分保护动物权利。而那些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为动物的遭遇(比如美国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冲击华人家禽店等现象)流下的眼泪更像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爱心的怜悯;况且,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还伤害到了他人的“人权”。
正如作者所说,有的人能从猫的眼里看见尼罗河的源头,但有的人不能。这已经无所谓了,反正谁也无从确认沉默的动物是否承认自己的眼里有河流还是有别的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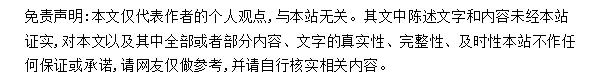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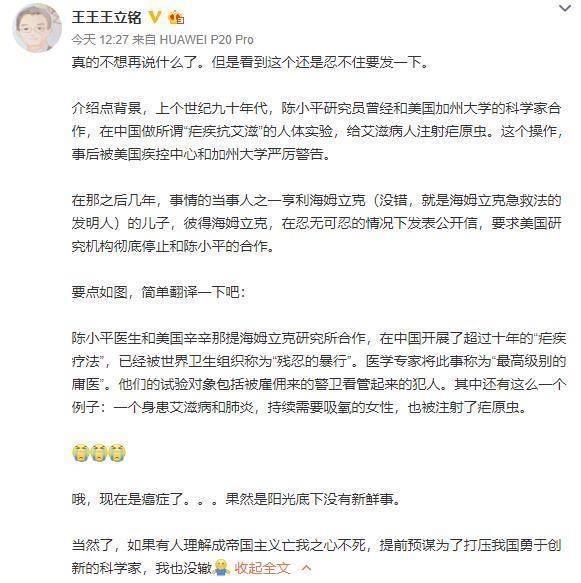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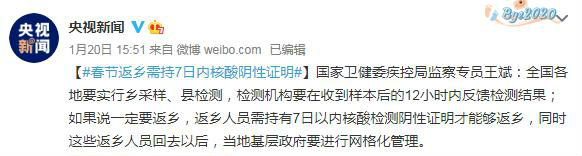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