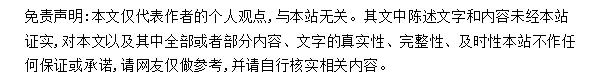在我的故乡,六月是夏天的代称,不是单指一个月份。也怪,故乡将春天、秋天、冬天一概唤作本名,唯独把夏天叫六月。北方的春、秋都短,不过是冬与夏的过渡,专门用来播种和收割,农事结束,季节也就完结。六月和冬天最长。冬天是农家的闲日,叫做冬闲,但冬闲单调,是躲在屋子里的无所事事,不如六月的闲广阔多姿。
六月有儿童节。童年的这个节日感觉像过年,有新衣穿,有好吃食。我们穿上白衬衣(虽大多是粗布漂白)、学生蓝的裤子,系上红领巾。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几分零花钱,买一根冰棍两分钱,还有剩余。母亲总是给我一角钱,我再从父亲抽屉里偷二两粮票,六分钱、二两粮票,就能从供销社饭店买一个糖馅馒头。还有“春晚”呢——那天学校不上课,开联欢会,孩子们在操场坐成一片白,像一群纯洁的白鸽。
六月水暖,可以到河里洗澡。可是作为月份的六月,水还凉,不能下水。但毕竟有了借口,过了“六一”,就扑通通跳进河里,身体舒展成漂浮的青蛙。大人发现了,揪着耳朵拎回家。那时孩子们往往理直气壮:“不是六月了吗,为啥不能洗澡?”小小年纪就会偷换概念,假装不知此六月非彼六月。
六月可捕鱼。捕鱼其实是淘鱼,孩子们把田间的水沟用土坝住,截成一段,用桶把水淘干;大人甚至把一条河拦腰坝上,一桶一桶地淘水。淘鱼是个力气活,也仿佛是一项工程。水淘干了,鱼儿露出脊梁,在泥泞里穿梭逃窜。
六月插完了稻秧,收拾了麦子,种了晚玉米,就不再有大规模的农事了,只剩下给花生薅草,给玉米施肥等零星小活儿,可以悠悠地做。这时闲日子就到了。烈日当空,知了在树上嘶鸣,狗在树荫里吐舌头,整村的人都在午休,白天竟似夜般安静。
倒是夜里像煮开了锅,家家都到街上乘凉,搬着板凳、蒲团,拿上芭蕉叶的凉扇,围成人堆。一条街上,隔不远就是一堆人,远远望去,若那街是一条河流,人堆就是漂浮的一条又一条的船;若是蜿蜒的长城,人堆就是一座一座的烽火台。凡有人的地方,就有一堆烟火,虽不是狼烟,不能御敌,却能驱赶蚊子。六月的蚊子像嗡嗡的战斗机,对我们狂轰滥炸。我们唯有用麦秸点起一堆火,覆上青草,火区出呛人的青烟,蚊子才会落荒而逃。
老人们摇着凉扇讲乡村往事,有点文化的讲《聊斋》。孩子们终究熬不到半夜,在大人怀里,或者在草席上就睡着了。大人把孩子抱回家,放进蚊帐,又跑回街上去乘凉。有的干脆夜不归屋,到房顶上睡觉,高处总是凉快。
六月的闲,有着沸腾的童年温度。立秋之后,这温度虽还能顺延数日,但抵不住凉风蔓延。我们很伤感。不像冬天将去,我们会兴奋;春天消逝,秋天完结,在孩子眼里,都不如六月的消退触痛心灵。小孩子经常这样对话:“你喜欢六月还是冬天?”一概答:“喜欢六月,冬天太冷。”“可是六月很热。”“热也比冷好受。”孩子们喜欢有温度的日子。
以前,六月过去了,带走的是一个季节,来年还会有一个六月,如今感觉,六月是永远过去了,带走的是一个时代。譬如河流干了,无处洗澡、淘鱼;街上再无乘凉之人,室内干净凉爽,有空调、电视和网络,谁会躺到街上去?孩子们也不对“六一”有感觉了,如今节日太多,动辄以吃、穿为主题,谁还会在乎一个儿童节?甚至我都有点怀念蚊子。我住楼房几十年了,几乎都忘了蚊子的模样。
唯一不变的是称呼,夏天依然被唤作六月。有一次我和乡亲交谈,随口说出“夏天”二字,他们大眼瞪小眼,分明是在讥笑我,好像我忘了本,不该那么文绉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