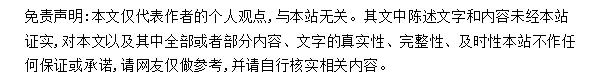上大学之前我很少吃到真正的辣。对于潮汕人来说,平日里蘸点沙茶酱,撒点胡椒粉,这就是辣,肉里鱼里偶尔夹杂几丝红色灯笼椒,与其说是配味,倒不如说是为了装饰。潮汕人不爱吃辣,主要是怕“热气”,家里常循着节候的变化煲些“青草水”,也就是凉茶,比如“春葱(指荸荠)、夏莲、秋芦(芦根)、冬葛(葛根)”等等。
大学时我们班有六个男生,住在一间宿舍,其中老二是四川人,老三是湖南人,每次回校都会带来家里特制的大瓶辣酱。看他们吃得很香,我也学着掰开花卷馒头,将辣酱涂抹上去,果真胃口大开。我后来敢讨个川妹子当媳妇,应该和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四川人管辣椒叫“海椒”,我岳父岳母帮我们带孩子,跟我们在深圳住了十多年,每次从蜀地回来,旅行包里总少不了干辣椒干花椒,他们嫌这里买的“不正宗”。他们把带来的干辣椒干花椒焙脆捣碎,滚了油做成了辣椒油花椒油,用起来更方便。那会儿我家是一楼,有个大阳台,摆着一张石桌,夏天我们爱在阳台吃饭,好多同事熟人路过都探过头来闲聊几句,他们很惊讶我们为什么会吃那么多菜。我岳母总是念叨着某某邻居,买菜只买一点点,她去买菜,别人总以为她是开餐馆的。有句话老挂在她的嘴边:“把生活‘开’好!”这大概也是他们大半辈子沉淀下来的生活哲学吧。我岳父岳母都十分好客,我们的朋友一来更是红彤彤地摆满一桌,蒸炒烧煎煮,外加凉拌,个个麻辣鲜香。
冬天到了,我们家阳台就会拉起好几根绳子,挂上岳父岳母自制的腊肠腊肉腌鱼,红的紫的褐的黄的白的,如一道彩帘隔在我们和行人中间,常引得他们驻足观看赞叹,仿佛年味也近了。我岳母有空就会走到阳台,像个将帅巡视军队那样看着她的“产品”,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摇头:“深圳的天气是有些热。”
几乎每个四川人都是烹饪高手,男人比女人似乎更“得行”。我到岳父母家,通常是大舅哥掌勺,其他人只负责娱乐,聊天、嗑瓜子、打麻将、看电视。要是有谁到厨房重地露个脸,就会被他善意地“轰”出去。川菜中,口水鸡、酸菜鱼还有腊肠腊肉都是我爱吃的,尤其是毛血旺,有用鸭血的也有用猪血的,不仅入口嫩滑,还能找到入味的毛肚、黄喉、鳝段这样的“杂碎”。我太太的嫂子是凉拌鸡高手,每次都让她来做这道菜。口水鸡不仅要求煮鸡的火候要把握得恰好,对作料调制的要求也很高,要做到麻辣适中、鲜香嫩爽不说,还得弹牙不腻。川菜之中,我唯独不太喜欢甜烧白,就是将红豆沙夹着半透明的五花肉、下面堆着红糖糯米饭,蒸至松软香糯作为甜食上桌,老人们很爱吃。几乎每一席酒碗都少不了甜烧白,我想它跟潮州菜的白果芋泥或者糕烧番薯芋是一样的,以甜味寓意生活的美好。
我不善饮酒,而四川人几乎个个都是“酒仙”,我第一次以女婿的身份来到四川露脸,几桌子的亲友都过来跟我干杯,多亏岳父和大舅哥替我挡酒。我大舅哥面不改色地说:“他们广东人不是这么喝酒的,要举着高脚杯小口小口地喝。”老岳父也替我证实:“他是个文化人,只会写文章画画,不会喝酒。”这些过分夸大的话竟也被亲友们宽容地接受了。
我到太太的同学家去,她的丈夫已经失业一年,一家三口的生活用度全由她负担,听说我们来了,男主人跑到外面拎了只鸡回来,给我们做了满满一桌川菜。我本想安慰他们几句,没想到这两口子甚为乐观,男主人还说自己一点都不着急,正好在家做做饭,辅导孩子功课,享受一下自由自在。我太太有个发小,有一年一个人跑到深圳来,给我带来十多个双流最有名的兔头,在我家边喝冰啤酒边用“川普”教我如何啃兔头,先把上下颚掰开,咬出兔舌再吃兔腮,然后啃兔脸,吃干净外部的肉最后吮脑花……我以为他是来旅游的,结果是最近发了笔小财,听说深圳的服装新潮,就飞过来买几件回去,第二天我太太陪他逛了华强北还有另外几个大商场,听说他一口气买了十几件,当晚就飞回成都了。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物产丰富,历史上人们生活相对安定,日子也就过得逍遥些。四川人大都是乐天派,喜欢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既不焦虑也不匆忙,随处是打得噼里啪啦的麻将、熙攘红火的茶馆、热气腾腾的火锅、摆龙门阵的声浪……最是人间烟火气,丝丝缕缕暖人心。寻常而又有趣,这也许才是最好的活法,光想一想都觉得好安逸。